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洪升长生殿的问题,以及和写《长生殿》的人。到底是“洪升”还是“洪升”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长生殿》是洪升啼血之作,为何却为他招致下狱之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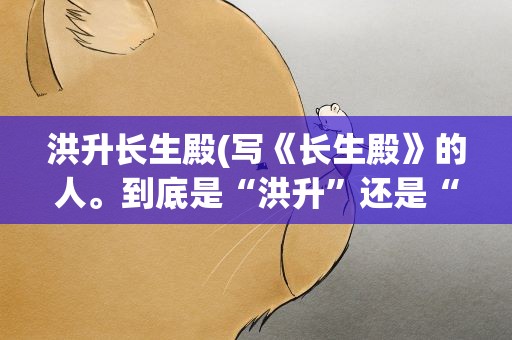
清初诗人、大戏曲家洪升最初写有剧本《沉香亭》,后改至为《舞霓裳》,最后历经十年,定稿于《长生殿》,这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剧本一经问世,便引起朝野轰动。据《柳南随笔》记载,在当时,内聚班为京城第一戏班,洪升《长生殿》写好后“授内聚班演之。大内览之称善,赏诸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藩称之。于是诸王府及各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如内赐,先后所获殆不赀。”
有了最高统治者高度好评与大力宣扬,《长生殿》几乎是垄断了当时的演出市场,“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长生殿》徐麟序)。“内聚班”因为演《长生殿》取得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他们对洪升深怀感激:“赖君新制,吾获赏多矣。请张宴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邀之俱来。”
其时正当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秋前夕,而洪升出生于1645年8月21日(农历是七月初一),正好是又过节又祝寿,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于是洪升邀请了他在朝中做官的好友赞善赵执信、侍读学士朱典、侍讲李澄中、台湾知府翁世庸以及同是太学生的查嗣琏、陈奕培等五十余人前来观戏。可是这班人光想着过节祝寿了,却忘了这还处在佟皇后刚宾天的国丧禁乐期间,曲终戏散之后,
大祸临头了,有人上奏朝廷,“谓是日系国忌,设宴张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结果“奏入,得旨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洪升被捕下狱,最后革去国子生籍。居《康熙起居注》记载,洪升此时已是候选县丞,一旦革去学籍,什么功名、候补县官都同时丧失了,再也不会有当官(补天——文人的理想)为民造福的机会了。赵执信年少得志,官运中天,却从此布衣终生;被牵涉落难者达五十余人。
大家想一想,在封建社会,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如要实现最低的理想,比如要振兴家族(曾经辉煌过的),还不说治理天下、为民造福等宏愿,首先你得走仕途,仕途的路径一旦掐断了,你永远就是一介平民,甚至更糟。洪升在京城求学、滞留长达二十余年,也就是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坚持在想踏入仕途这条路径中了,一夜之间,这种坚持被拦腰砍断,精神和肉体一下子全部跌入谷底,不在其中,不知其痛,
谁也无法想象这种给支撑人生精神世界带来的毁灭性打击的痛苦是怎样的深重。而这种深重的痛苦,长时间的反思,内心真正情感的爆发,三者合一,才是产生《红楼梦》这样一部熔经历、警戒、让人性大释放于一炉的巨作的根本原因,平平之辈焉能成就?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洪升二十余年在京求学、
候任,是他无法抗拒的外部原因造成的,从诗文和剧作中,反映最多的是他的情子情种的才子本色,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家庭的压力,有足够可以养活一家人的资本,他根本不会去求官走仕途,他就是一个多情才子,一个思如泉涌的文人!而这一切,都通过他笔下的《红楼梦》喷涌而出了。
“演《长生殿》招祸案”,虽有大量史籍记载,但在时间、地点、遭难人数、起因等说法上多有歧义。通过梳理、对比,笔者认为时间、人数基本可以定局,从《红楼梦》的一些隐喻描写上也可以互为对应作证。演出地点主要有洪寓、生公园、查楼三说。查楼基本也可以排除,因为只有《清史列传》是这样记载,孤证不立;洪升在京寓所,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理由有两条:
一,洪升是太学生,怎有象样的住房?即便是候选县丞,政府也不会先分配同样级别的房子吧?没有象样的房子,怎来的“观者如云”(赵执信语)?
二,演《长生殿》,需要很大的场面和开销,非一般人家可以承受。王友亮在《双佩斋集》中记载“国初巨富”亢氏“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初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他举称是。”亢氏是清初盐商,扬州旧有“亢园”,占地极广,时人呼为“百间房”(见《扬州画舫录》)。厉鄂在《樊谢山文房文集·书项生事》记载了一名“项生”的优人在某江淮大吏家中演出《长生殿》之事,
其演出排场极尽奢靡。虽说洪升不会自掏腰包,但大场面大气派总要吧?不然怎么体现伶班的诚意呢?而生公园(又称太平园)正是当时京城历史最悠久的戏园,在此上演无须另搭戏台、重置座椅、安排候场化妆间等演戏必备的条件的,如在洪寓上演,
置办这些东西不仅难以想像,动静闹得很大也不符合当时环境和人的心理,在民间戏园上演不就驾轻就熟顺理成章吗?一唯强调《康熙起居注》的官方记载并不十分可靠,记录者对地点也有随意想像或听说记录的可能,并不一定去实地调查确认。当然只有王应奎、董潮是持生公园说,金埴等多人是持洪寓说的。
写《长生殿》的人。到底是“洪升”还是“洪升”
洪升
洪升(1645~1704)清代戏曲作家、诗人。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南屏樵者。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生于世宦之家,康熙七年(1668)北京国子监肄业,二十年均科举不第,白衣终身。代表作《长生殿》历经十年,三易其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问世后引起社会轰动。次年因在孝懿皇后忌日演出《长生殿》,而被劾下狱,革去太学生籍,后离开北京返乡。晚年归钱塘,生活穷困潦倒。康熙四十三年,曹寅在南京排演全本《长生殿》,洪升应邀前去观赏,事后在返回杭州途中,于乌镇酒醉后失足落水而死。洪升与孔尚任并称“南洪北孔”。
所以肯定是洪升,不然就不是“南洪北孔“,而是“南升北孔
洪升的长生殿的主题思想
有人把“长生殿”完全看作是歌颂封建帝王生活、供统治阶级玩赏的作品,毫无现实性、人民性可言,因而,认为提出纪念洪升是不正确的。有人从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主义和超阶级的“人性论”的观点来肯定“长生殿”,认为:“长生殿”把李隆基和杨玉环之间的爱情,表现得异常真挚诚笃;所描写的杨玉环是一个善良、温柔,同时也是聪明、勇敢的妇女形象;月宫重圆的收场,表现了爱情战胜了死。有人谈“长生殿”只列举出像“疑谶”、“进果”和“骂贼”等几出明显地同情人民疾苦的戏,说明“长生殿”值得肯定的意义,而对整个作品则缺乏全面的分析,因此,对“长生殿”价值的理解,也就是比较表面的。有的地方举行纪念会,只介绍洪升的生平事迹,对“长生殿”的内容和为什么要纪念他的问题,却避开不谈。
长生殿”的创作,作者主要地是想表现一个真挚、生死不渝的爱情。这是以前讨论“长生殿”的人的一种传统的看法。
长生殿”后半部,基本上可以说是失败之作。
洪升否认“女色亡国”的论调,却把罪过完全推之于“逆藩奸相”,这种看法当然仍然是表面的。但,“长生殿”的伟大,却在于它形象的反映出了封建王朝灭亡前夕的昏溃、腐败的影象。
“长生殿”的创作,显然是要来抒写兴亡之恨。对剧中人物的描写,忠于祖国的得到表扬,危害祖国的受到惩罚。虽然,把天宝之乱,隐喻作明清间的变化并不确当,但,在它上面,确是凝结着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同时,在“长生殿”许多地方,都接触到了人民生活的苦难;对危害人民的事物的讽刺与抨击,也或多或少的凝结着人民的思想和愿望。所以,“长生殿”与人民的思想是有着联系的。
在“长生殿”中,也时时流露出作者主观意识中的封建思想和唯心的“情”的观念。在前半部,客观现实的真实描写占着主导地位;但,在后半部中,它就上升为主导的地位,使作品坠入到了虚幻中去,成为空虚的、无意义的东西。当然,后半部也有着几出如“骂贼”、“弹词”好戏,但,那只是个别的。
“长生殿”前半部,从主题思想、结构等方面看,是可以独立,而无损于艺术的完整性的。
以上,仅就“长生殿”的内容,作了简单的分析,至于“长生殿”在艺术性上所达到的成就,这里就不再赘述。
OK,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